繼承法相關問題研究
〔據以研究的案例〕
遺贈人潘剛鐸系潘鄧氏的次子,曾因盜竊罪于1982年10月被判刑,1998年12月刑滿釋放后,居住在沈陽市東陵區汪家鎮李巴彥村,1999年7月起潘剛鐸與董麗男同居生活。2000年10月13日潘剛鐸書寫《鄭重聲明》一份,內容為:“我自1999年8月份建房以來,無論在資金上,還是在勞力方面,我的朋友董麗男都給予了大量的支援和幫助,特在此鄭重聲明,如果我以后在人身安全方面出現過重的傷或亡?我的朋友董麗男將享有我的全部家產,全部歸她所有,其他兄弟姐妹均無權占有,為以防后顧,特此聲明。2000年10月13日潘剛鐸。”2001年8月8日董麗男與其前夫鄧國經沈陽市大東區民政局登記離婚后,與潘剛鐸繼續同居生活。2001年10月9日潘剛鐸駕車與他人相撞死亡,其個人負事故的主要責任,潘鄧氏從肇事對方處得到死亡賠償金6,000元。潘剛鐸生前有存款人民幣1,000元、平房七間(房內無間壁墻、192平方米),門市房、廂房各兩間(均無產籍證明),上述三外房屋位于同一院落。潘剛鐸死亡后,董麗男一直居住在潘剛鐸遺留的兩間無產籍廂房內,并在農村信用社提取了潘剛鐸生前存款人民幣1,000元。
潘鄧氏于1920年4月3日出生,系農民,生有三兒一女,潘剛鐸生前,潘鄧氏在其女兒家居住,由潘剛鐸的兩個哥哥給付生活費。
潘剛鐸因建房于1999年1月22日、6月17日分兩次向李巴彥村民委員會借款人民幣10,000元;2001年5日13日潘剛鐸在段艷萱處購買水泵件,欠貨款人民幣699元未付。
2002年1月15日潘鄧氏向沈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繼承潘剛鐸全部遺產,判令董麗男退還所占用的房屋。段艷營、李巴彥村民委員會得知后,亦分別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在潘剛鐸的房產處理價款中,償還其生前所欠債務。原審法院將此三案合并審理。
一審法院審理中,委托有關部門對《鄭重聲明》進行筆跡鑒定,結論為:《鄭重聲明》中的兩組“潘剛鐸”簽名及正文均為潘剛鐸本人所寫。同時,法院委托有關鑒定部門對爭議遺產進行了評估,兩間無產籍門市房估價為8,638元,七間平房估價為17,918元。兩間廂房,經潘鄧氏、董麗男協商估價為3,000元。
一審法院認為:遺贈人潘剛鐸生前自書的“鄭重聲明”,有具體內容及遺贈人潘剛鐸本人的簽名,并注明了形成的時間,符合自書遺囑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且在審理過程中又經有關部門鑒定系其本人所寫,可見遺贈人潘剛鐸此份自書遺囑系其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遺囑繼承的效力優于法定繼承,潘鄧氏要求確認其是唯一合法繼承人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但考慮到潘鄧氏是遺贈人潘剛鐸的親生母親,現又年老體弱,缺乏勞動力,生活確有困難,可適當分得遺贈人潘剛鐸的遺產份額。村委會、段艷萱要求從潘剛鐸的遺產中償還其生前欠款人民幣10,000元、人民幣699元的主張,證據充分且符合法律規定,予以支持。故判決如下:一、遺贈人潘剛鐸的遺產平房七間、門市房兩間、廂房兩間、存款人民幣1,000元歸董麗男所有。二、董麗男于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給付潘鄧氏人民幣10,000元。三、董麗男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給付第三人李巴彥村民委員會人民幣10,000元。四、董麗男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給付第三人段艷萱人民幣699元。五、鑒定費人民幣3,600元,由潘鄧氏承擔人民幣2,050元,董麗男承擔人民幣1,550元。六、駁回潘鄧氏及第三人李巴彥村民委員會的其它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850元,由潘鄧氏承擔人民幣810元,董麗男承擔人民幣860元,第三人李巴彥村民委員會承擔人民幣180元。
潘鄧氏對一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其主要上訴理由為:董麗男是有夫之婦,與潘剛鐸是非法同居關系,《鄭重聲明》是一種惡意串通的遺贈,是違反公序良俗的民法基本原則的無效行為,不應受到法律的保護。
在董麗男答辯期間,潘鄧氏因病去世,其生前留有代書遺囑,故二審法院按潘鄧氏的遺囑,更換其長子潘增鐸、兒媳孫英為本案上訴人,二審法院審理中,二人沒有提出新的上訴主張。
二審法院認為:潘剛鐸所寫的《鄭重聲明》,涉及了其個人財產的處理問題,應按自書遺囑對待,現無任何事實和法律依據證明該遺囑無效,因此在該遺囑生效且董麗男以自己的行動表明接受遺贈時,對潘剛鐸的遺產應按遺囑內容處理。但在該遺囑生效時,潘剛鐸的生母潘鄧氏已81周歲高齡,自己本身沒有諸如養老金、退休金等收入,需依靠子女贍養而生活,屬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根據《繼承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在遺產處理時,應當給潘鄧氏留有必要的份額,剩余的部分方可按照潘剛鐸遺囑確定的分配原則處理,由董麗男清償潘剛鐸生前所欠債務后接受遺贈。由于一審宣判后,潘鄧氏提出上訴后去世,其生前已以代書遺囑的形式確定了其遺產的繼承人、受贈人,故本院按照其遺囑內容,對原判決部分條款予以變更,判決潘鄧氏所享有的必留份財產由潘增鐸繼承、孫英受贈,潘鄧氏在本案中應承擔的義務,由潘增鐸、孫英承擔。故判決:一、維持一審判決的第一、三、四項;二、變更一審判決的第二項為:董麗男于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給付潘鄧氏的遺產繼承人潘增鐸、遺產受贈人孫英人民幣10,000元;三、變更一審判決的第五項為:鑒定費人民幣3,600元,由潘增鐸、孫英承擔人民幣2,050元,董麗男承擔人民幣1,550元。四、變更一審判決的第六項為:駁回潘增鐸、孫英及第三人李巴彥村民委員會的其它訴訟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850元,由潘增鐸、孫英承擔人民幣810元,董麗男承擔人民幣860元,第三人李巴彥村民委員會承擔人民幣180元。二審案件受理費1,850元,由潘增鐸、孫英負擔。
〔相關問題研究〕
本案是一起涉及有關遺贈的效力、必留份權人的確定及份額、被繼承人債務清償順序、遺囑繼承等《繼承法》上規定的或未明確規定的法律問題和民法上的民事行為是否有效、法律適用的方法和順序等諸多法律問題的較為復雜的民事案件。
一、關于潘剛鐸遺贈行為的效力問題,本案在法律適用上應否直接適用民法基本原則作為處理案件的依據問題。這是本案雙方當事人爭議最大的焦點問題。
首先,《繼承法》賦予了公民遺囑自由的權利。該法第十六條三款規定:“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據此,任何一個公民生前均有權依法處分其個人所有的合法財產,除違反該法第十九條必留份的規定應該受到限制外,只要遺囑是有行為能力的人所寫、是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形式符合法律規定、未處分他人財產,就應該認定為有效。本案潘剛鐸所立的該份遺囑,無論從他本人的行為能力、意思表示、遺囑形式,還是其處分的財產,均符合繼承法的明文規定,除未給潘鄧氏保留必要的份額應該受到部分限制外,未侵害國家、集體或者其他任何人的利益,其余部分應認定有效。
其次,《繼承法》中對受贈人的身份和主體資格沒有限制性規定,董麗男的婚外同居行為雖為《婚姻法》所否定,但該法對婚外同居者受贈他人財產的權利也未加以限制,而且本案雖然潘剛鐸書寫該份遺囑時,董麗男是有夫之婦,與潘剛鐸是婚外同居關系,但在該份遺囑生效時,董麗男已與其前夫登記離婚,其作為單身女子與單身男子的潘剛鐸的非婚同居關系,雖不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提倡,但現行的法律、法規中并沒有禁止性規定,因此其有權受贈潘剛鐸所留的該份遺產。
再次,公序良俗是我國《民法通則》總則中的規定,而《繼承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按照法律適用的方法,只有在爭議的問題特別法中沒有規定的情況下才可適用普通法的規定,而本案是繼承糾紛案件,《繼承法》已賦予公民立遺囑將其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任何人的權利,潘剛鐸立遺囑將其財產贈與董麗男的行為,是有法可依的,不屬于特別法沒有明文規定、應該適用普通法的情形;退一步講,即使本案存在適用《民法通則》的條件,也應該首先適用分則中有關民事行為效力的規定,該法第五十八條一款(五)規定“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屬無效民事行為,而本案潘剛鐸立遺囑將其財產贈與董麗男的行為,并不涉及國家基本制度、根本利益和社會穩定等方面要求的社會公共利益,因此不能適用該條規定認定遺囑無效。此外,《民法通則》第七條規定的“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是倡導性規范,在當今社會還不能以行為人的行為不符合道德規范,就認定該行為違法、無效。因此,本案不能撇開《繼承法》的具體明文規定,而直接適用《民法通則》的總則規定認定遺贈行為無效。
綜上,本案潘剛鐸所寫的《鄭重聲明》,無論在形式上、內容上,還是在成立要件上,均符合《繼承法》的明文規定;《婚姻法》對非婚同居及相互間的贈與行為沒有禁止和處罰性規定;《民法通則》對無效民事行為的認定也有明文規定,上述三個法律對遺囑人將其個人所有的財產遺贈給與其同居的人均沒有禁止性規定,因此潘剛鐸將其財產以遺囑形式遺贈給董麗男的行為,不屬于法無明文規定或者遺漏的現象,因此在裁量上不能直接適用民法基本原則作為處理案件的依據。
二、關于必留份權人的確定及份額問題
必留份,也叫特留份。我國現行的《繼承法》第十九條規定:“遺囑應當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十七條規定:“遺囑人未保留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的遺產份額,遺產處理時,應當為該繼承人留下必要的遺產,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參照遺囑確定的分配原則處理”。由此可見,我國《繼承法》對必留份權人及份額問題的規定很籠統,對哪一順序的繼承人可以享有必留份權的問題沒有界定,對必留份的份額、占遺產總額的比例也沒有任何限定,這就給法官以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
世界上許多大陸法系的國家對必留份權人的范圍、必留份份額的規定極為明確。如《法國民法典》即規定了直系卑親屬和直系尊親屬享有特留份,而且對卑親屬、尊親屬的特留份數額做了分別規定,如該法第913條規定:“如財產處分人死后僅留有一子(女),其生前贈與或遺囑贈與之方式處分的財產不得超過其所有財產一半,如其留有子(女)二人,其有權以此方式處分的財產不得超過其所有財產的三分之一;如其留有子(女),三人或三人以上,其可處分的財產不得超過本人所有財產的四分之一。”該法第914條規定:如死者無子女,但在父系與母系兩系中均有一名或數名直系尊血親,其以生前贈與或遺囑處分的財產不得超過其所有財產的一半;如處分人僅在一親系中留有直系尊血親,其可處分的財產不得超過其所有財產的四分之三。”《德國民法典》規定直系血親卑親屬、尊親屬及配偶均享有特留份。就份額問題,該法第2303條規定:(1)如果被繼承人的一個晚輩直系血親被死者處分排除于繼承順序之外,則他可以向繼承人要求特留份額。特留份份額為法定繼承份額價值的半數;(2)被繼承人的父母和配偶若被死者處分排除于繼承順序之外,同樣享有上述權利。
三、關于被繼承人的債務和遺贈的清償順序問題。
被繼承人死亡后,其遺產上的債務除其生前所欠的債務(欠繳的稅款和債務)外,還包括繼承人因其繼承人身份而應予承擔的債務,尤其是因必留份、遺贈、遺托而產生的債務。在這些債務并存時,哪個應優先清償,我國繼承法的規定與世界各國的規定即有相同,也有不同。
1、關于被繼承人的債務、遺贈和必留權清償的順序。就此問題,我國《繼承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執行遺贈不得妨礙清償遺贈人依法應當繳納的稅款和債務。”也就是說在被繼承人生前欠繳稅款或留有債務的情況下,首先應當清償其依法應當繳納的稅款和債務之后,才能執行遺贈。世界上大陸法系的國家對此問題的規定基本一致,形成了一則格言,即“無論何人非清償債務后,不得為遺贈”。
2、關于被繼承人的債務、遺贈和必留份權清償的順序,我國《繼承法》的規定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規定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61條規定:“繼承人中有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人,即使遺產不足清償債務,也應為其保留適當遺產,然后再按《繼承法》第三十三條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條的規定清償債務。”可見,我國繼承法對三項債務清償的順序應當理解為:必留權清償在先、被繼承人債務清償在后、遺贈清償為最后。
但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則規定:必留份應以積極財產為計算基礎,即應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所有遺產扣除債務后之剩余額為標準,決定必留份的數額;必留份、遺贈應在被繼承人其他債務清償之后得為清償;在被繼承人的諸多債務中,被繼承人生前所欠債務應優先受償,因被繼承人生前贈與所生債務為次,因特留份權所生債務為再次,遺贈所生之債務為最后。尤其是《德國破產程序外債務人行為撤銷法》第三條規定:“繼承人由遺產對于特留份請求權、遺贈或負擔為履行時,遺產債權人于破產程序就遺產順序先于或等于給付受領人者,得如同繼承人之無償處分,撤銷之。”
盡管我國繼承法對于被繼承人的債務、遺贈和必留份權清償的順序的規定與其他國家規定的不一致,但對于遺產大于債務的案件來說,三者還是都可以得到清償的,只是數額多少的問題。本案即是根據必留份權人潘鄧氏還有其他三名子女贍養的實際,在遺產總額為30,556元、遺產債務為10,699元的情況下,確定潘鄧氏的必留份份額為10,000元,其余財產由受贈人董麗男償還潘剛鐸生前債務10,699元后,接受遣贈財產9,857元。這樣處理的結果是遺產債務占遺產總額三分之一多一點、必留份清償近三分之一、遺贈清償近三分之一。這一結果,即符合我國繼承法的規定,也符合世界各國關于三項債務清償的順序和份額的基本原則。
四、關于遺囑繼承問題。
本案必留份權人潘鄧氏在提起上訴后因病去世,其生前留有代書遺囑,將其財產留給長子潘贈鐸繼承、長媳孫英受贈。因此本案二審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十二條“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沒有表示放棄繼承,并于遺產分割前死亡的,其繼承遺產的權利移轉給他的合法繼承人”的規定,直接更列潘贈鐸、孫英為上訴人,在二人沒有提出新的上訴主張的情況下,作出終審判決。判決潘鄧氏在本案中因必留份所享有的財產10,000元,由潘增鐸繼承、孫英受贈;鄧氏在本案中應承擔的交納案件受理費和鑒定費的義務,由潘增鐸、孫英承擔。
〔結論〕
鑒于我國繼承法對必留份權人的范圍及份額規定的不明確,筆者認為,結合我國國情,《繼承法》就此問題應當加一修改。
就必留價權人的范圍,應規定:“第一順序、第二順序繼承人中及繼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繼承人生前扶養、贍養、撫養的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人均可享有必留份”。這一規定是有法律依據的,因為我國現行《繼承法》第十四條就明確規定:“對繼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繼承人扶養的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人,可以分給他們適當的遺產”。
就必留份數額問題,應當以積極財產為計算基礎,即應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所有遺產扣除債務后之剩余額為標準,決定必留份的數額。具體數額的計算可以參照我國現行的人身損害賠償標準計算,即以當地公布的城鎮或農村居民人均生活費為計算依據,未成年人,計算至其十八周歲為止;六十周歲以上的,必留份數額為: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或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20-增加的歲數);七十五周歲以上的,按五年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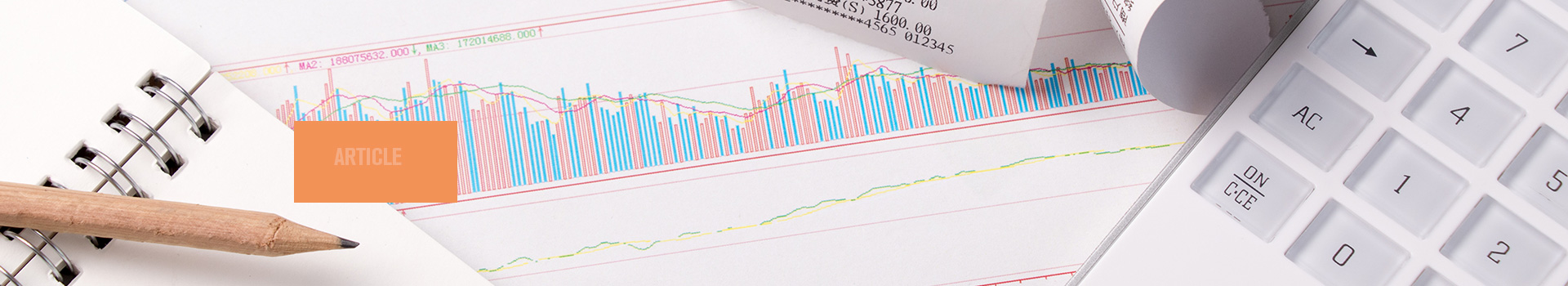
 上海家暢離婚律師網
上海家暢離婚律師網

 滬公網安備:
滬公網安備:

